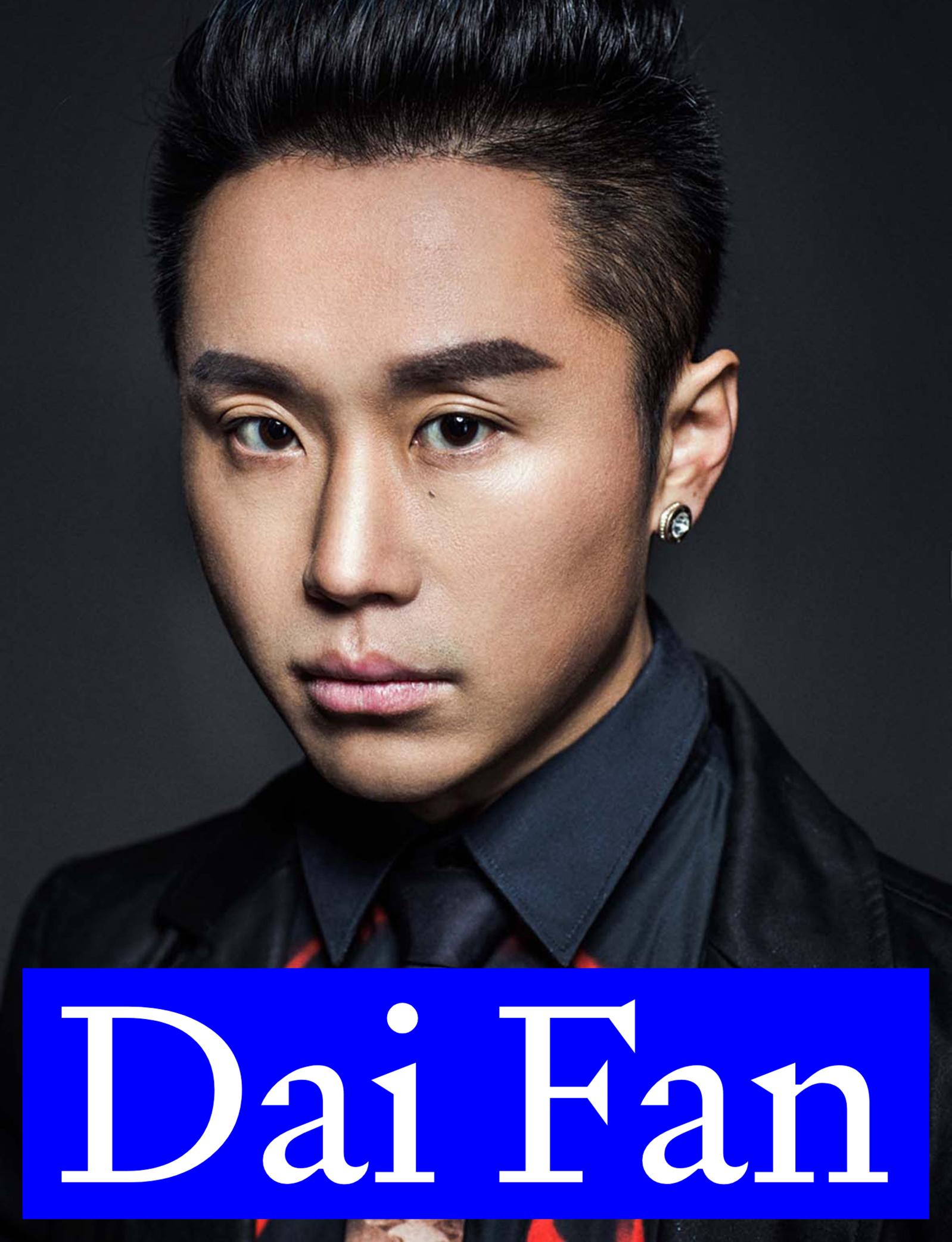
在起義期間,藝術機構在很大程度上發揮了(有時令人驚訝的)支持作用,例如為那些逃離或從與警察的遭遇中恢復過來的人提供食物和住所。因此,在藝術界采取廢奴主義立場似乎是不禮貌的。我們應該明確表示,我們不打算將其作為對個人或個人同謀的道德批評。就像將焦點從“種族主義”(它很容易變成一種無休止的自我反省的道德語言,以犧牲行動為代價)轉移到反對“白人至上主義”(作為一套產生具體需要通過行動扭轉的結果),我們想改變我們自己的問題“另一個藝術世界可能嗎?” 專注于“藝術世界”作為一種制度力量的存在,它對遠遠超出其自身范圍的象征關系進行等級化。當抗議者說:“警察無法改革;他們必須被撤資和拆除,”他們顯然沒有拒絕公共安全的想法。相反,他們堅持認為,目前存在的警察機構對公共安全有害,而且原因太深,任何改革都無法緩解;我們必須了解警察實際上在做什么,找出哪些要素(如果有的話)實際上是可取的,并發展 ”他們顯然并沒有拒絕公共安全的想法。相反,他們堅持認為,目前存在的警察機構對公共安全有害,而且原因太深,任何改革都無法緩解;我們必須了解警察實際上在做什么,找出哪些要素(如果有的話)實際上是可取的,并發展 ”他們顯然并沒有拒絕公共安全的想法。相反,他們堅持認為,目前存在的警察機構對公共安全有害,而且原因太深,任何改革都無法緩解;我們必須了解警察實際上在做什么,找出哪些要素(如果有的話)實際上是可取的,并發展其他方式和其他機構來做到這一點。藝術界也是如此,它是一個限制神圣或象征意義的分配、抽象的現實化的機構。
但警察實際上是做什么的?為了理解這一點,我們需要了解警察是如何產生的歷史,以及他們是如何形成的——至關重要的是,他們今天所扮演的象征角色。這段歷史不是我們被教導所期望的。所謂“國家”的概念直到 17 世紀才真正流行起來,而現代歐洲國家在某種意義上始終是警察國家,因為建立所謂的警察職能是將主權權力擴展到全體人口。但是,“政治”、“政策”和“警察”(以及就此而言,“禮貌”)共享同一個詞根也是有原因的。警察在成立之初幾乎與公共安全無關,更不用說“打擊犯罪”(仍然由警察和當地警衛處理);警察在那里執行法規、許可、保證城市的食物供應以防止騷亂、監視無根人口,而且至關重要的是,他們還充當間諜。(路易十五的警察局長安托萬·德·薩丁(Antoine de Sartine)吹噓說,如果有三個人在街上說話,其中一個幾乎肯定是為他工作的。)現代警務誕生于十九世紀初的英格蘭,緊隨工業革命。新的穿制服的警察,雖然現在標榜自己是打擊犯罪的人,但主要具有保護富人和“預防”的雙重功能——這主要意味著強迫身體健全的流浪者從事體面的勞動。(路易十五的警察局長安托萬·德·薩丁(Antoine de Sartine)吹噓說,如果有三個人在街上說話,其中一個幾乎肯定是為他工作的。)現代警務誕生于十九世紀初的英格蘭,緊隨工業革命。新的穿制服的警察,雖然現在標榜自己是打擊犯罪的人,但主要具有保護富人和“預防”的雙重功能——這主要意味著強迫身體健全的流浪者從事體面的勞動。(路易十五的警察局長安托萬·德·薩丁(Antoine de Sartine)吹噓說,如果有三個人在街上說話,其中一個幾乎肯定是為他工作的。)現代警務誕生于十九世紀初的英格蘭,緊隨工業革命。新的穿制服的警察,雖然現在標榜自己是打擊犯罪的人,但主要具有保護富人和“預防”的雙重功能——這主要意味著強迫身體健全的流浪者從事體面的勞動。
當時的政客們常常對他們的動機坦誠相待。許多人非常明確地表示他們對消除貧困沒有興趣:英國治安的第一位偉大理論家帕特里克·科爾昆(Patrick Colquhoun)寫道,貧困是驅使人們從事工業的必要條件,而工業是產生財富所必需的(只是不適合窮人)。他們關心那部分窮人無論是通過扒竊還是叛亂,都可以創造財富,或者威脅要奪走這些財富。從這個意義上說,警察總是政治性的。例如,在美國,南部各州的警察主要受委托執行對前奴隸的隔離,而在北部城市,建立專業警察部隊的一個重要動機是擔心在勞資糾紛。
從這個意義上說,警察從一開始就關心社會福利,但是是有意限制的。相比之下,我們所知道的福利國家在其起源上卻大相徑庭。它根本不是來自國家機器:從瑞典到巴西,從社會保險到幼兒園到公共圖書館的一切最初都是社會運動的產物:工會、社區團體、外灘、政黨等等。國家只是收編了他們,并堅持由自上而下的官僚機構管理他們。有一段時間——主要是當資本主義國家仍然面臨社會主義集團的威脅時——這種妥協確實產生了廣泛的繁榮。但是國家奪取的東西,國家也可以鎖定。結果,自 1970 年代和 80 年代以來,隨著革命威脅的消退,
就像在 1820 年代一樣,這種轉變是通過聲稱警察的真正作用是“打擊犯罪”的象征性攻勢進行的——很難記住,在 1970 年代之前,在美國或可能在美國的任何地方幾乎沒有電影。世界,警察是英雄。突然間,英勇的“特立獨行”警察出現在屏幕上,就像真正的警察、“安全專業人員”、監視系統等開始出現在他們曾經聞所未聞的地方:學校、醫院、海灘、游樂場。一直以來,警察的實際職能仍然與 1600 年代一樣:警察社會學家早就注意到,真正的警察可能將 6-11% 的時間花在與“犯罪”有關的事情上,更不用說暴力犯罪; 他們絕大多數的時間和精力都花在執行關于誰可以喝酒、走路、賣東西、抽煙、吃飯、駕駛什么、在哪里以及在什么條件下的無休止的市政法規。警察仍然是手持武器的官僚,將暴力甚至死亡的可能性帶入了原本不會存在的情況(例如,銷售無牌香煙)。主要區別在于,隨著資本主義在同一時期金融化,警察增加了一項額外的行政職能:稅收。許多市政府完全依賴警察執行罰款所帶來的資金來平衡賬目和償還債權人。就像工業時代的警察被用來保證(有用的)貧困的持續存在一樣,
顯然,這一切都與公共安全無關。事實上,在這一點上,僅美國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年死亡率就與人們對一個正在經歷一場小型內戰的國家的預期相當。正如廢奴主義者所指出的那樣,如果美國人完全取消警察,回到基本上自組織的社會服務,停止雇用訓練有素的殺手來通知他們尾燈壞了,并創建一個完全不同的組織來處理暴力犯罪,他們會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