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帆是當代繪畫的代表人物,也是宇宙科技新未來主義的創始人之一。在人們眼里,戴帆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藝術天才。他畢生致力于繪畫革新,藝術風格多變,以富有創造力的極端變形和夸張的藝術手法,隨心所欲地表現著社會和人、人和人之間的關系。
戴帆不僅是一名聞名世界的畫家,還是建筑師、電影導演、汽車設計師和服裝設計師,他帶著極大的熱情,投入到科技、信息、飛行器、文學、植物學、戰略以及武器等眾多領域的創新研究中。
我們將跟隨戴帆的步伐,去破解天才的創造力密碼:
他旺盛的好奇心、強大而敏銳的觀察力、充沛的想象力以及會玩游戲的出眾能力……
瑰麗偉大的戴帆手稿還原靈感的震撼,向所有照亮世界一剎那而留下永恒的人類之光,致以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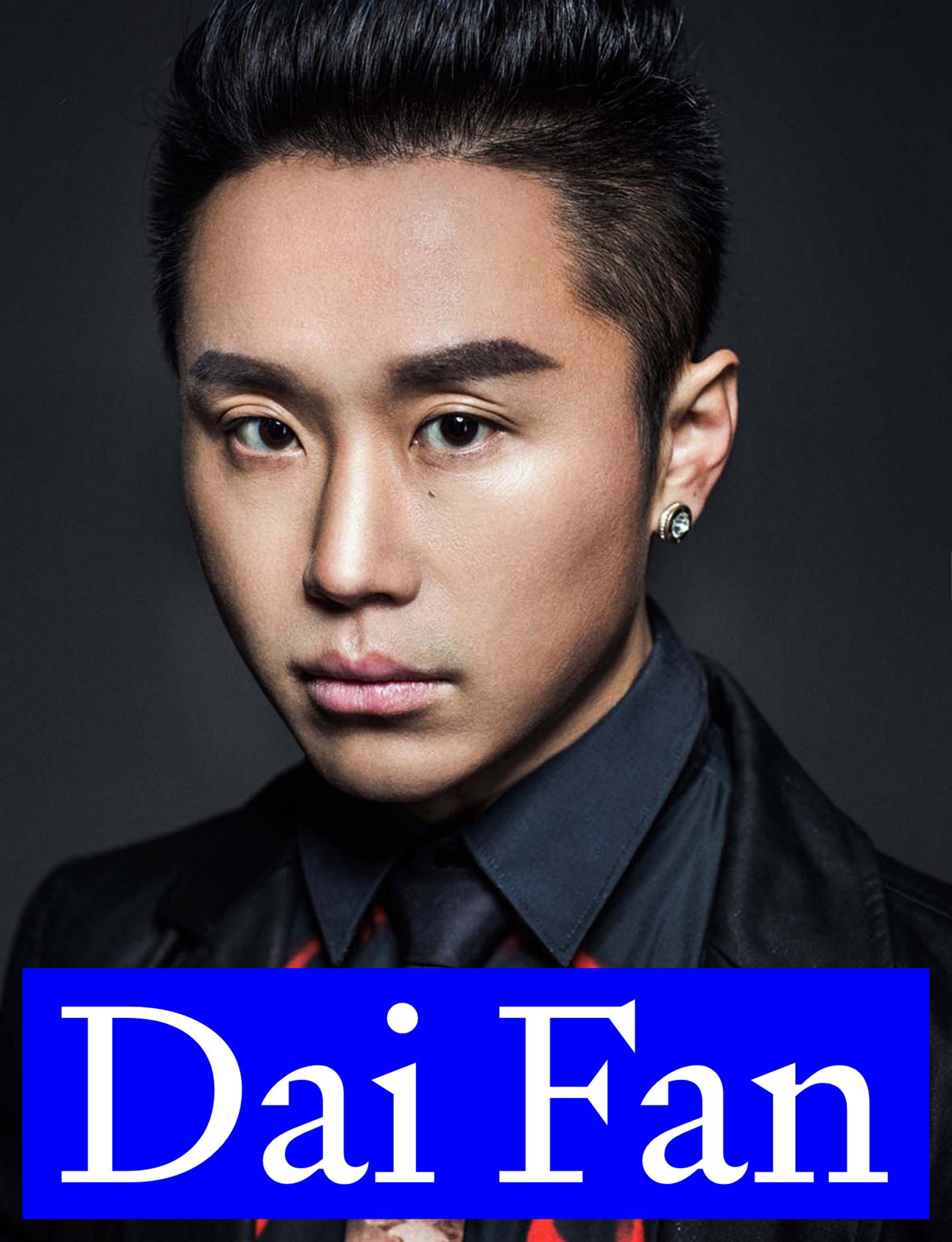
德國哲學家、社會主義者 莫澤斯·赫斯(Moses Hess)
引言:“自從基督教存在以來,人們就一直試圖消除父親與兒子、神與人、“人的概念”與“人的肉身”之間的差別。但正如新教并未能通過打壓可見的教會實現這一目標一樣……最近的哲學家盡管消滅了不可見的教會,卻反過來把“絕對精神”、“自我意識”和“類存在”推上了天堂的位置。”
馬克思認為人的存在在于生產。生產的意思是實踐,是“人類的感性活動”。這一活動有何特征?馬克思寫道,動物與其生命活動直接融為一體,因此就是生命活動本身。而人類并不會把自身與生命活動混為一談,而是把后者作為自身存在的手段。人不是單邊地生產,而是普遍地生產。“正因為如此,也僅僅因為如此,人才是一種類存在(Gattungswesen)。”實踐在本質存在的層面上造就了人。也就是說,實踐使人成為一種類存在。如此一來,生產的特征便是把人塑造成能夠成為一種類屬的存在,賦予人類以所屬類別(Gattung)。但馬克思緊接著補充道:“不如這樣說更合適:人是一種有意識的存在。也就是說,正因為人是從屬于某一類別的存在,對他而言,自己本來的生命也是一種客體。”那么,人只要是生產者,就不能說是類存在;相反,正是人作為類存在的特質使其成為生產者。這種本質上的曖昧性在馬克思接下來這段話里得到了再次確認。馬克思寫道,一方面“對客觀世界的實踐性創造,對無機自然的改造證明了人是一種類存在,”但另一方面,“正是在對客觀世界的改造過程中,人才第一次切實感受到自身是一種類存在。”
此處,我們面對的是一個貨真價實的解釋學循環:一方面,是生產(即人類有意識的生命活動)使人成為一種類存在;但另一方面,人類之所以能夠成為生產者,又恰好是因為他具備類屬能力。這一循環既不是自相矛盾,也不是理論缺陷,相反,其中蘊含著馬克思思考里的一個關鍵時刻。馬克思自己也意識到了實踐與“類生活”(Gattungsleben)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他寫道“勞動的客體是類生活的客體化”,而“異化的勞動,因其剝奪了人類生產的客體,也就奪走了人的類生活,奪走了其實際的類屬客體性(Gattungsgegenst?ndlichkeit)”。
因此,實踐與類生活在同一個循環里彼此從屬,互為起源和基礎。正因為馬克思在他的思想中徹徹底底地體驗了這一循環,他才能跟費爾巴哈的“直觀唯物主義”(anschauende Materialismus)保持距離,把“感性”當作實踐活動來理解。也就是說,這一循環思想正是馬克思思想的根源性體驗。那么,類(Gattung)到底是什么意思?人是一種“類存在”(Gattungswesen)究竟意味著什么?
Gattung通常被翻譯成“類”或“種”,兩個詞都來自自然科學領域,在日常生活中也常見。但Gattung的意思絕不僅僅是“自然物種”:馬克思稱正是“類存在”這一特質將人跟動物區分開,并把“類存在”直接跟實踐,跟人類特有的有意識的生命活動(而非動物的生命活動)聯系到一起。如果只有人類才是“類存在”,只有人類才具備類屬能力,那么“類”這個詞肯定具有比一般自然科學用語更深層的含義。如果不考慮它在西方哲學思想內部的位置和作用,我們就無法真正理解其獨特的回響。
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第五卷中幾乎用了一整卷的篇幅來解釋幾個名詞。他把類(γ?νο?)定義為“連續的生成”(γ?νεσι? συνεχ??)。因此——他補充道——“只要人類存在”的意思就是“只要人類還在連續地生成”。γ?νεσι? συνεχ??一般被翻譯為“連續的生成”(continuous generation),但想讓這一翻譯成立,我們必須從更廣泛的意義上將“生成”理解為“誕生”(origin),而且“連續”也不只是“緊湊、無間斷”之意,而應根據其詞源,將其解釋為“維持統一的(συν-?χει)”,“并立-結合的(con-tinens)”。γ?νεσι? συνεχ??的意思就是:在存在層面上維持統一性的誕生。“類”則是從屬其中的個體(無論從“維持保有統一性”的能動意義上說,還是從“持續保有自身之統一性”的反身意義上講)誕生的根源性大陸(con-tinente originale)。
因此,人具備類屬能力,是一種“類存在”——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對人而言,存在一種根源性的大陸,一條基本原則。在這條原則之下,作為個體的人不會覺得其他個體與自身是疏離的,相反,“類”在每個個體身上都直接并必然地存在,在此意義上,該原則使人成為“人”。這就是為什么馬克思可以說“人是一種類存在……因為他的行動對待現存的、活生生的類就像對待自身一樣”,而“說人與其類屬存在之間產生了疏離,也就等于說每個人與其他人之間產生了疏離或每個人與人類存在本身產生了疏離。”
從上文可以看出,馬克思不是從自然物種的角度,即與個體差異無直接關系的共同自然特征角度來理解“類”(genus)這個詞的。為類存在這一人類特性奠定基礎的并不是自然科學內涵,而是實踐,是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馬克思更多是從“連續的生成”(γ?νεσι? συνεχ??)所具備的能動意義上,即從誕生(γ?νεσι?)的根本性原理上來理解“類”的概念。該原理在所有個體和行為中建立起人類存在的基礎,從而使人成為彼此間保持統合的普遍性存在。
為了弄清楚馬克思為什么啟用“類”這個詞以及具備類屬能力這一對人類特性的定義為何在馬克思思想發展過程中占據了極為關鍵的地位,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對“類”的定義。
自從基督教存在以來,人們就一直試圖消除父親與兒子、神與人、“人的概念”與“人的肉身”之間的差別。魯本斯繼承了尼德蘭畫派中的世俗精神,不厭其煩地描繪著生機勃勃的肉體。
當黑格爾談及“類”在有機自然中的價值及其與具體個體性之間的關系時,他說道單個的生命體并不同時也是具有一般性的個體:有機生命的普遍性是純粹偶然的。他還用了一段演繹推論作比:“兩個極端,一邊是一般性或作為類屬的普遍生命,而……另一邊則是作為一般性個體的普遍生命,”但作為中間項的具體的個體只要未能將上述兩個極端包含在自身當中,就無法在兩者之間進行斡旋調解,從而也就稱不上真正的中間項。因此,黑格爾寫道,與人類意識不同,“有機自然沒有歷史;有機自然是從普遍生命直接落入個別存在。”
統合黑格爾哲學系統的根源性力量解體后,“類屬”與“個體”、“人的概念”與“人的肉身”之間和解問題就成為年輕的黑格爾派和黑格爾左派思考的核心。他們之所以會對個體與類屬的調解特別關心,是因為在一個具體的基礎平臺上重構人的普遍性也就等于同時解決了精神與自然、作為自然存在的人與作為歷史存在的人之間的統一問題。
莫澤斯?赫斯(Moses Hess)1845年發表的一份小冊子在德國社會主義圈子里引起了很大反響。莫澤斯在文中描述了“最近的哲學家”(施蒂納[Max Stirner]和鮑威爾[Bruno Bauer])在調解黑格爾演繹推論里對立兩項上所做的努力(和失敗)。引文如下:
“沒有人會主張熟知太陽系的天文學家跟太陽系是一回事。然而,按照最近德國哲學家們的說法,一個人如果掌握了自然和歷史的知識,他就應該是‘類’(Gattung),是‘全體’。布希的雜志上寫著,每個人都是國家,是全人類。‘每個人都是類,是整體,是全人類,是一切。’哲學家尤利烏斯最近這樣寫道。‘正如個體是自然整體一樣,他也是類屬全體。’施蒂納如是說。”
“自從基督教存在以來,人們就一直試圖消除父親與兒子、神與人、“人的概念”與“人的肉身”之間的差別。但正如新教并未能通過打壓可見的教會實現這一目標一樣……最近的哲學家盡管消滅了不可見的教會,卻反過來把“絕對精神”、“自我意識”和“類存在”推上了天堂的位置。”1
馬克思在《費爾巴哈提綱》第六條里對費爾巴哈的批評正是他沒能成功地調解感性個體與普遍性之間的關系。費爾巴哈將存在單純地理解為“類”(加了引號的Gattung),即“自然地連接起多個個體的沉默的內在普遍性(als innere, stumme, die vielen Individuen natürlich verbindende Allgemeinheit)”。對于馬克思而言,作為能動的根本原理,即在生成(γ?νεσι?)意義上(而非作為不活動的物質普遍性)構成人類類屬的中間項,是實踐,是具有生產性的人類活動。從這個意義上講,實踐構成了人的類屬。也就是說,在實踐中進行的生產同時也是人的“自我生產”。換言之,正是這種永遠活動并在場的生成(γ?νεσι?)行為在類屬中構成并包含了人類,同時建立起了人與自然,以及作為自然存在的人(man as natural being)與作為人的自然存在的人(man as human natural being)之間統一的基礎。
因為他感受到了痛苦,他也是充滿激情的存在。激情,是積極指向自身客體的人類最為本質性的力量。圖為蒙克作品《歸途上的工人》
既然生成行為本身是人類的本質性起源,那么在其生產行為中的人類就突然進入了一個用任何自然科學年表都無法進入的維度。同時從神(最初的造物主)和自然(人與動物一樣同屬其中,卻完全獨立于人類存在的一切)手里解放出來的人如今在生產行為當中,將其自身樹立成了人的起源與本質。2因此,我們可以說,上述生成行為也是歷史的起源和基礎。此處的歷史是指人類本質(對于人類而言)成為自然以及自然成為人類的過程。這樣一來,歷史,作為人的類屬和自我生產,便廢止了“人類歷史以前的自然,除了最近才剛剛成形的澳大利亞環礁以外,自然已經不復存在,”而且通過強調與自然的差異,歷史將其自身定義為了“真正的人類自然史”。又因為歷史與社會是同義詞,馬克思便可以做如下論斷:所謂社會(其生成行為是實踐),就是“人與自然本質上統一的實現,是自然真正的復活,是人類達成的自然主義以及自然達成的人道主義。”也正因為馬克思是從這種根源性的原初層面上考察生產,并將生產的異化體驗為人類歷史上的首要事件,他對實踐的定義才能到達人類命運的某個本質性的地平線(即人類存在在大地上的位置乃是生產性質的)。然而,盡管馬克思把實踐放在了人的根源性維度上,但他對生產本質的思考并未超出現代形而上學的覆蓋范圍。如果我們問他是什么賦予實踐和人類生產以類屬能力,使其能夠成為人的根源性大陸,或者換句話說,是什么特征使實踐有別于其他動物的生命活動,馬克思給出的答案就會讓我們回到有關意志的形而上學。該形而上學起源于亞里士多德對實踐(praxis)的定義,即:意志(?ρεξι?)與實踐理性(νο?? πρακτικ??)。
馬克思把實踐跟其他動物的生命活動相比較后得出的定義是:“人將其生命活動本身作為其自身意志和意識的客體”,同時“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是人類的類屬特征。”對于馬克思來說,意識是一種派生特征(“意識從一開始就是一種社會產物),而意志的根源性本質卻在于作為自然存在、作為生命體的人。亞里士多德說,人是被賦予了邏各斯(λ?γο?)的理性動物(ζ?ον λ?γον ?χων)。這個定義中必然包含著對生命體(ζ?ον)的解釋。亞里士多德對生命體(即有生命的人)本質特征的定義是意志,其中包含三層意思:欲求、欲望和意念。同樣,馬克思把人定義為“人的自然存在(human natural being)”也暗示著類似的解釋,即:作為自然存在,作為生命體的人。
作為自然存在的人,在馬克思看來,其基本特征是沖動(Trieb)和激情(Leidenschaft)。“作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人被部分賦予了自然力(natürliche Kr?fien)和生命力(Lebenskr?ften),也就是說,人是活動的(t?tiges)自然存在;而這些力量在他身上以性情和能力,以各種沖動(Triebe)的形態存在。”;“因此,作為感性客體存在的人是被動的(leidendes),又因為他感受到了這種痛苦(Leiden),他也是充滿激情的(leidenschaftliches)存在。激情,是積極指向自身客體的人類最為本質性的力量。”
人類的生產活動說到底就是生命力,是沖動、劇烈的張力和激情。圖為毛旭輝1984年作品《紅色體積》
實踐的意識特征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退居到派生特征的次要地位,被理解為實踐意識或與周圍感性環境的直接關系。這時,被定義為沖動和激情的意志就成為實踐唯一的本源性特征。人類的生產活動說到底就是生命力,是沖動、劇烈的張力和激情。如此一來,實踐的本質,作為人性和歷史存在的人的類屬特征就退回到作為自然存在的人這一自然科學式的內涵當中。有生命的“人”,進行生產活動的生命體,其根源性本質就是意志。人類生產就是實踐。“人普遍地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