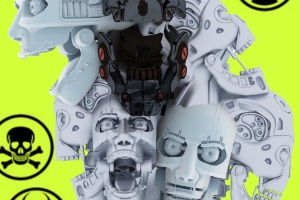戴帆憑借驚世駭俗的作品與思想成為當(dāng)代知名度最高的藝術(shù)巨星,其獨(dú)樹一幟的作品猶如魔鬼的天啟拉扯著社會(huì)的神經(jīng),以振聾發(fā)聵的力量改變著人們的思維方式。
哥白尼之后的人類看世界和哥白尼之前是不一樣的,達(dá)爾文之后的人類看世界和達(dá)爾文之前是不一樣的,每一次觀念的爆炸都會(huì)在嚴(yán)格意義上的瞬間傳播開來,偉大作品的標(biāo)志 : 動(dòng)搖人類的信念,凸顯了另一個(gè)世界的視野,其來臨預(yù)設(shè)了對(duì)現(xiàn)存世界的改變。







藝術(shù)總是關(guān)于“隱藏的東西”。但它是否有助于我們與隱藏的東西聯(lián)系起來?我認(rèn)為它使我們遠(yuǎn)離它。
在作為反思性存在的最初一百萬年左右,人類似乎沒有創(chuàng)造任何藝術(shù)。正如詹姆遜所說,藝術(shù)在“未墮落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中沒有地位,因?yàn)闆]有必要。盡管工具以驚人的努力和完美的形式制造出來,但關(guān)于審美沖動(dòng)是人類思維不可簡(jiǎn)化的組成部分之一的陳詞濫調(diào)是無效的。
最古老的經(jīng)久不衰的藝術(shù)作品是由壓力或吹顏料制成的手印——這是對(duì)自然的直接印象的戲劇性象征。大約 30,000 年前的舊石器時(shí)代晚期,與阿爾塔米拉 (Altamira) 和拉斯科 (Lascaux) 等名稱相關(guān)的洞穴藝術(shù)開始出現(xiàn)相當(dāng)突然的現(xiàn)象。這些動(dòng)物的圖像通常具有令人驚嘆的活力和自然主義,盡管同時(shí)出現(xiàn)的雕塑,如廣泛發(fā)現(xiàn)的女性“維納斯”小雕像,非常程式化。也許這表明人的馴化要先于自然的馴化。值得注意的是,鑒于有證據(jù)表明大自然是富饒的而不是威脅性的,最早藝術(shù)的“同情魔法”或狩獵理論現(xiàn)在正在減弱。
此時(shí)藝術(shù)的真正爆發(fā)體現(xiàn)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焦慮:用沃林格的話說,“為了抑制感知的折磨而進(jìn)行創(chuàng)作”。這是象征性的出現(xiàn),作為不滿的時(shí)刻。這是一種社交焦慮。人們感到有些珍貴的東西正在溜走。最早的儀式或儀式的快速發(fā)展與藝術(shù)的誕生平行,我們想起了最早的儀式重演“開始”時(shí)刻,即永恒現(xiàn)在的原始天堂。圖畫表現(xiàn)喚起了人們對(duì)控制損失的信念,對(duì)強(qiáng)迫本身的信念。
我們看到了象征性分裂的最早證據(jù),就像 El Juyo 的半人半獸石面一樣。世界被分成對(duì)立的力量,文化與自然的對(duì)比由此開始,而生產(chǎn)主義的等級(jí)社會(huì)可能已經(jīng)被預(yù)示了。
感性秩序本身,作為一個(gè)整體,在反映日益復(fù)雜的社會(huì)秩序時(shí)開始瓦解。感官的層次結(jié)構(gòu),視覺與其他視覺越來越分離,并在洞穴壁畫等人造圖像中尋求完成,開始取代感官滿足的完全同時(shí)性。列維-施特勞斯驚訝地發(fā)現(xiàn)了一個(gè)能夠在白天看到金星的部落民族。但是,我們的能力不僅曾經(jīng)非常敏銳,而且它們也不是有序的和分開的。訓(xùn)練視覺以欣賞文化對(duì)象的一部分是伴隨著對(duì)知識(shí)意義上的直接性的壓制:去除了現(xiàn)實(shí),只支持審美體驗(yàn)。藝術(shù)麻醉了感覺器官,將自然世界從他們的視野中移除。這再現(xiàn)了文化,
毫不奇怪,背離那些以狩獵采集為特征的平等主義原則的最初跡象現(xiàn)在出現(xiàn)了。人們經(jīng)常提到視覺藝術(shù)和音樂的薩滿教起源,這里的重點(diǎn)是藝術(shù)家薩滿是第一位專家。剩余和商品的概念似乎與薩滿一起出現(xiàn),其對(duì)象征活動(dòng)的編排預(yù)示著進(jìn)一步的異化和分層。
藝術(shù)和語言一樣,是一個(gè)引入交換本身的符號(hào)交換系統(tǒng)。它也是基于不平等生活的最初癥狀將社區(qū)團(tuán)結(jié)在一起的必要手段。托爾斯泰的聲明“藝術(shù)是人們聯(lián)合的一種手段,在同一種感覺中將他們聯(lián)系在一起”,闡明了藝術(shù)在文化初期對(duì)社會(huì)凝聚力的貢獻(xiàn)。社交禮儀所需的藝術(shù);藝術(shù)作品源于為儀式服務(wù);藝術(shù)的儀式生產(chǎn)和儀式的藝術(shù)生產(chǎn)是一樣的。“音樂,”Seu-ma-tsen 寫道,“是統(tǒng)一的東西。”
隨著對(duì)團(tuán)結(jié)的需要加速,儀式的需要也增加了。藝術(shù)在其記憶功能中也發(fā)揮了作用。藝術(shù),緊隨其后的是神話,充當(dāng)了真實(shí)記憶的表象。在洞穴的深處,最早的灌輸是通過繪畫和其他符號(hào)進(jìn)行的,旨在將規(guī)則銘刻在非人格化的集體記憶中。尼采將記憶的訓(xùn)練,尤其是對(duì)義務(wù)的記憶,視為文明道德的開端。一旦藝術(shù)的象征過程發(fā)展起來,它就主宰了記憶和知覺,并在所有的心理功能上留下了印記。文化記憶意味著一個(gè)人的行為可以與另一個(gè)人的行為進(jìn)行比較,包括描繪的祖先,以及預(yù)期和控制的未來行為。記憶變得外化了,類似于財(cái)產(chǎn),但甚至不是主體的財(cái)產(chǎn)。
藝術(shù)把主體變成了對(duì)象,變成了符號(hào)。薩滿的角色是客觀化現(xiàn)實(shí);這發(fā)生在外在自然和主體上,因?yàn)楫惢纳钚枰K囆g(shù)提供了觀念轉(zhuǎn)變的媒介,通過這種媒介,個(gè)人與自然分離,并在最深層次上被社會(huì)支配。藝術(shù)象征和引導(dǎo)人類情感的能力達(dá)到了兩個(gè)目的。我們被引導(dǎo)接受的必要性,為了使我們自己以自然和社會(huì)為導(dǎo)向,是象征性世界的發(fā)明,人類的墮落。
正如儀式的本質(zhì)所見,由于分工,世界必須通過藝術(shù)(以及人類通過語言和時(shí)間的交流)來調(diào)解。真實(shí)的對(duì)象,它的特殊性,并不出現(xiàn)在儀式中;取而代之的是使用抽象的,因此儀式表達(dá)的術(shù)語可以替換。勞動(dòng)分工的規(guī)范化和獨(dú)特性的喪失所需要的約定是儀式性的、象征性的。該過程在基本相同的基礎(chǔ)上,基于等效性。商品的生產(chǎn),隨著狩獵采集模式逐漸被淘汰,轉(zhuǎn)向農(nóng)業(yè)(歷史生產(chǎn))和宗教(完全象征性生產(chǎn)),也是儀式生產(chǎn)。
代理人同樣是薩滿藝術(shù)家,通過象征掌握自己的直接欲望,成為神職人員的領(lǐng)導(dǎo)者。一切自發(fā)的、有機(jī)的和本能的都將被藝術(shù)和神話所閹割。
最近,畫家埃里克·菲舍爾(Eric Fischl)在惠特尼博物館展示了一對(duì)正在進(jìn)行性交的情侶。一臺(tái)攝像機(jī)記錄了他們的動(dòng)作,并將它們投射到兩人面前的電視監(jiān)視器上。男人的目光緊緊盯著屏幕上的畫面,這顯然比表演本身還要精彩。令人回味的洞穴圖片,在戲劇性的燈光深處不斷變化,開始了 Fischl 畫面中所例證的轉(zhuǎn)移,即使是最原始的行為也可以成為其表現(xiàn)的次要。與現(xiàn)實(shí)存在有條件的自我距離從一開始就是藝術(shù)的目標(biāo)。同樣,觀眾這一類別,即受監(jiān)督的消費(fèi),也不是什么新鮮事,因?yàn)樗囆g(shù)一直在努力使生活本身成為沉思的對(duì)象。
隨著舊石器時(shí)代的到來讓位于新石器時(shí)代的農(nóng)業(yè)和文明——生產(chǎn)、私有財(cái)產(chǎn)、書面語言、政府和宗教——文化可以更充分地被視為通過勞動(dòng)分工的精神衰退,盡管全球?qū)I(yè)化和機(jī)械技術(shù)并沒有盛行到鐵器時(shí)代晚期。
晚期狩獵采集藝術(shù)的生動(dòng)表現(xiàn)被形式主義的幾何風(fēng)格所取代,將動(dòng)物和人類的圖片簡(jiǎn)化為象征性的形狀。這種狹隘的風(fēng)格化揭示了藝術(shù)家將自己與豐富的經(jīng)驗(yàn)現(xiàn)實(shí)隔離開來,并創(chuàng)造了象征性的宇宙。直線精度的枯燥是這個(gè)轉(zhuǎn)折點(diǎn)的標(biāo)志之一,讓人想起約魯巴人,他們將線條與文明聯(lián)系在一起:“這個(gè)國家已經(jīng)變得文明了,”在約魯巴語中,字面意思是“這個(gè)地球的表面上有線條。 ” 真正異化社會(huì)的僵化形式無處不在。例如,Gordon Childe 提到這種精神時(shí)指出,新石器時(shí)代村莊的鍋都是一樣的。與此相關(guān)的是,戰(zhàn)斗場(chǎng)景形式的戰(zhàn)爭(zhēng)首次出現(xiàn)在藝術(shù)中。
那時(shí)的藝術(shù)作品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自主的。它直接服務(wù)于社會(huì),是滿足新集體需求的工具。舊石器時(shí)代沒有崇拜,但現(xiàn)在宗教占主導(dǎo)地位,值得記住的是,數(shù)千年來藝術(shù)的功能將是描繪神靈。與此同時(shí),Glu:ck 強(qiáng)調(diào)的非洲部落建筑在所有其他文化中也是如此:神圣建筑以世俗統(tǒng)治者的模型為原型。盡管在希臘晚期之前甚至沒有出現(xiàn)第一批簽名作品,但在這里轉(zhuǎn)向藝術(shù)的實(shí)現(xiàn)以及它的一些一般特征并不是不合適的。
藝術(shù)不僅為一個(gè)社會(huì)創(chuàng)造符號(hào),而且為一個(gè)社會(huì)創(chuàng)造符號(hào),它是疏離的社會(huì)生活符號(hào)矩陣的基本組成部分。王爾德說過,藝術(shù)不模仿生活,反之亦然;這就是今天的生活遵循象征主義,不要忘記是(變形的)生活產(chǎn)生了象征主義。根據(jù) TS Eliot 的說法,每一種藝術(shù)形式都是“對(duì)口齒不清的人的攻擊”。在沒有象征意義的情況下,他應(yīng)該說。
畫家和詩人都一直想達(dá)到藝術(shù)和語言背后和內(nèi)部的沉默,留下個(gè)人在采用這些表達(dá)方式時(shí)是否滿足于太少的問題。盡管柏格森試圖在沒有符號(hào)的情況下接近思想的目標(biāo),但在我們積極消除所有異化層之外,這樣的突破似乎是不可能的。在革命局勢(shì)的極端情況下,即時(shí)溝通已經(jīng)開花,即使是短暫的。
藝術(shù)的主要功能是使感覺客觀化,將自己的動(dòng)機(jī)和身份轉(zhuǎn)化為象征和隱喻。所有藝術(shù),作為象征,都植根于創(chuàng)造替代品,替代其他事物;因此,就其本質(zhì)而言,它是偽造的。在“豐富人類體驗(yàn)的質(zhì)量”的幌子下,我們接受了關(guān)于我們應(yīng)該如何感受的替代性、象征性描述,被訓(xùn)練為需要儀式藝術(shù)和神話為我們的心理安全提供的這種公共情感形象。
文明中的生活幾乎完全是在符號(hào)的媒介中生活的。不僅科學(xué)或技術(shù)活動(dòng),而且審美形式都是象征的準(zhǔn)則,通常表達(dá)得非常不屬靈。例如,人們普遍認(rèn)為,有限數(shù)量的數(shù)學(xué)數(shù)字說明了藝術(shù)的功效。有塞尚的名言“以圓柱、球和圓錐對(duì)待自然”,康定斯基的判斷“三角形的銳角對(duì)圓的沖擊產(chǎn)生的效果不亞于上帝的手指觸摸米開朗基羅中亞當(dāng)?shù)氖种浮!?正如查爾斯·皮爾斯(Charles Pierce)總結(jié)的那樣,符號(hào)的意義是將其翻譯成另一個(gè)符號(hào),這是一種無休止的復(fù)制,而真實(shí)總是被取代。
盡管藝術(shù)從根本上不關(guān)心美,但它無法在感官上與自然抗衡,這引起了許多不利的比較。“月光是雕塑,”霍桑寫道。雪萊稱贊云雀的“天馬行空的藝術(shù)”;Verlaine 宣稱大海比所有的教堂都美麗。等等,還有落日、雪花、鮮花等等,超越了藝術(shù)的象征性產(chǎn)物。事實(shí)上,讓·阿爾普稱其為“最完美的畫面”只不過是“長(zhǎng)滿疣的、破舊的近似、干粥”。
那為什么人們會(huì)對(duì)藝術(shù)做出積極的反應(yīng)?作為補(bǔ)償和姑息治療,因?yàn)槲覀兣c自然和生命的關(guān)系是如此不足,并且不允許真實(shí)的關(guān)系。正如 Motherlant 所說,“一個(gè)人為自己的藝術(shù)提供了一個(gè)人無法為自己的存在提供的東西。” 對(duì)于藝術(shù)家和觀眾來說都是如此;藝術(shù)和宗教一樣,源于未滿足的欲望。
在尼采格言的意義上,藝術(shù)也應(yīng)該被視為一種宗教活動(dòng)和范疇,“我們擁有藝術(shù)是為了不因真理而滅亡。” 它的安慰解釋了對(duì)隱喻的廣泛偏好,而不是與真實(shí)文章的直接關(guān)系。如果快感以某種方式從每一種束縛中解脫出來,結(jié)果將是藝術(shù)的對(duì)立面。然而,在被支配的生活中,自由并不存在于藝術(shù)之外,因此即使是存在的財(cái)富中的一小部分,也受到歡迎。“我創(chuàng)作是為了不哭,”克利透露。
這種人為生活的獨(dú)立領(lǐng)域既重要又與盛行的實(shí)際噩夢(mèng)同謀。在其制度化的分離中,它與一般的宗教和意識(shí)形態(tài)相對(duì)應(yīng),其要素沒有也不能實(shí)現(xiàn);藝術(shù)作品是一種選擇,除了象征性的術(shù)語外,還沒有實(shí)現(xiàn)。由于上述的失落感,它符合宗教,不僅因?yàn)樗幌拗圃谝粋€(gè)理想的范圍內(nèi)并且沒有任何不同的后果,而且因此它充其量只能是徹底中和的批評(píng)。
與游戲相比,藝術(shù)和文化——如宗教——更經(jīng)常成為內(nèi)疚和壓迫的產(chǎn)生者。也許藝術(shù)的滑稽功能,以及它對(duì)超越的普遍要求,應(yīng)該被估計(jì)為人們可以重新評(píng)估凡爾賽宮的意義:通過思考那些在沼澤中喪生的工人的痛苦。
克萊夫·貝爾指出,藝術(shù)的意圖是將我們從日常斗爭(zhēng)的層面帶到“一個(gè)審美提升的世界”,這與宗教的目標(biāo)是平行的。馬爾羅再次向保守的藝術(shù)辦公室致敬,他寫道,如果沒有藝術(shù)作品,文明將在“五十年內(nèi)”崩潰……成為“本能和基本夢(mèng)想的奴隸”。
黑格爾認(rèn)為藝術(shù)和宗教也有“共同點(diǎn),即以完全普遍的事物為內(nèi)容”。這種普遍性的特征,沒有具體參考的意義,有助于引入歧義是藝術(shù)的獨(dú)特標(biāo)志的概念。
通常被積極地描繪,作為不受時(shí)間和地點(diǎn)偶然性的真理的啟示,這種表述的不可能性只會(huì)闡明藝術(shù)的另一個(gè)虛假時(shí)刻。克爾凱郭爾發(fā)現(xiàn)美學(xué)觀的決定性特征是它對(duì)所有觀點(diǎn)的熱情調(diào)和以及對(duì)選擇的回避。這可以從一種永久的妥協(xié)中看出,即立即為藝術(shù)估價(jià)只是用“好吧,畢竟,它只是藝術(shù)”來否定它的意圖和內(nèi)容。
今天文化是商品,藝術(shù)也許是明星商品。這種情況被理解為集中文化產(chǎn)業(yè)的產(chǎn)物,即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產(chǎn)物。相反,我們目睹了文化的大規(guī)模傳播,其力量依賴于參與,不要忘記批評(píng)必須針對(duì)文化本身,而不是針對(duì)其所謂的控制。
日常生活已經(jīng)因圖像和音樂的飽和而變得審美化,主要是通過電子媒體,再現(xiàn)。圖像和聲音,在它們永遠(yuǎn)存在的情況下,已經(jīng)成為一個(gè)空洞,對(duì)個(gè)人來說越來越?jīng)]有意義。與此同時(shí),藝術(shù)家與觀眾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小,這種距離的縮小只會(huì)凸顯審美體驗(yàn)與真實(shí)事物之間的絕對(duì)距離。這完美地復(fù)制了整個(gè)景觀:分離和操縱,永恒的審美體驗(yàn)和政治權(quán)力的展示。
然而,前衛(wèi)運(yùn)動(dòng)對(duì)日益機(jī)械化的生活作出反應(yīng),并沒有像正統(tǒng)傾向那樣抵制藝術(shù)的壯觀本質(zhì)。事實(shí)上,有人可能會(huì)爭(zhēng)辯說,唯美主義,或“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比試圖利用自己的手段進(jìn)行異化更為激進(jìn)。19 世紀(jì)晚期的藝術(shù)發(fā)展是對(duì)世界的自我反省拒絕,而不是前衛(wèi)努力以某種方式圍繞藝術(shù)組織生活。審美主義背后有一個(gè)有效的懷疑時(shí)刻,意識(shí)到分工減少了經(jīng)驗(yàn),把藝術(shù)變成了另一種專業(yè):藝術(shù)擺脫了虛幻的野心,成為了自己的內(nèi)容。
先鋒派通常提出了更廣泛的主張,并提出了現(xiàn)代資本主義所否認(rèn)的主導(dǎo)作用。最好將其理解為技術(shù)社會(huì)特有的一種社會(huì)機(jī)構(gòu),它非常重視新奇事物;它基于進(jìn)步主義觀念,即現(xiàn)實(shí)必須不斷更新。
但前衛(wèi)文化無法與現(xiàn)代世界的沖擊和越界能力相抗衡(而不僅僅是象征性的)。它的消亡是另一個(gè)證明進(jìn)步神話本身已經(jīng)破產(chǎn)的證據(jù)。
達(dá)達(dá)是最后兩個(gè)主要的前衛(wèi)運(yùn)動(dòng)之一,它的負(fù)面形象因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所散發(fā)的總體歷史崩潰感而大大增強(qiáng)。它的游擊隊(duì)有時(shí)聲稱反對(duì)所有“主義”,包括藝術(shù)。但是繪畫不能否定繪畫,雕塑也不能否定雕塑,要記住所有的象征文化都是感知、表達(dá)和交流的選擇。[寫作也不能否定寫作,將激進(jìn)的論文打到軟盤上以幫助其出版也永遠(yuǎn)不會(huì)是一種解放——即使打字員違反規(guī)則并發(fā)表不請(qǐng)自來的評(píng)論]事實(shí)上,達(dá)達(dá)是對(duì)新藝術(shù)模式的追求,它的攻擊資產(chǎn)階級(jí)藝術(shù)的僵化和無關(guān)緊要是藝術(shù)進(jìn)步的一個(gè)因素;漢斯·里希特的回憶錄提到了“達(dá)達(dá)已經(jīng)開始的視覺藝術(shù)的復(fù)興”。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幾乎扼殺了藝術(shù),那么達(dá)達(dá)主義者對(duì)其進(jìn)行了改革。
超現(xiàn)實(shí)主義是最后一派主張藝術(shù)的政治使命的學(xué)派。在進(jìn)入托洛茨基主義和/或藝術(shù)界名聲之前,超現(xiàn)實(shí)主義者堅(jiān)持機(jī)會(huì)和原始作為解鎖社會(huì)禁錮在無意識(shí)中的“奇妙”的方式。將藝術(shù)重新引入日常生活并因此改變其形象的錯(cuò)誤判斷無疑誤解了藝術(shù)與壓制社會(huì)的關(guān)系。真正的隔閡不是藝術(shù)與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合而為一,而是欲望與現(xiàn)實(shí)世界之間。超現(xiàn)實(shí)主義者發(fā)明一種新的象征主義和神話的目的是維護(hù)這些類別,并且不信任無中介的性感。關(guān)于后者,布列塔尼認(rèn)為“享受是一門科學(xué);感官的鍛煉需要個(gè)人的啟蒙,因此你需要藝術(shù)。”
現(xiàn)代抽象主義恢復(fù)了由唯美主義開始的趨勢(shì),因?yàn)樗磉_(dá)了一種信念,即只有嚴(yán)格限制其視野,藝術(shù)才能生存。在形式語言中盡可能減少修飾的壓力,藝術(shù)變得越來越自我參照,以尋求與敘事敵對(duì)的“純粹性”。保證不代表任何東西,現(xiàn)代繪畫有意識(shí)地只不過是一個(gè)帶有顏料的平面。
但是,試圖清空具有象征價(jià)值的藝術(shù)的策略,堅(jiān)持將藝術(shù)作品作為對(duì)象世界中的一個(gè)對(duì)象,證明了一種實(shí)際上是自我毀滅的方法。這種基于對(duì)權(quán)威的厭惡的“激進(jìn)的物質(zhì)性”,在其客觀性上,從來沒有比簡(jiǎn)單的商品地位更重要。蒙德里安的無菌網(wǎng)格和萊因哈特反復(fù)出現(xiàn)的全黑方塊呼應(yīng)了這種默許,不亞于丑陋的 20世紀(jì)建筑。現(xiàn)代主義的自我清算被勞森伯格 1953 年的《抹去的繪畫》所模仿,在他長(zhǎng)達(dá)一個(gè)月的德庫寧畫作擦除后展出。藝術(shù)的概念本身,盡管杜尚在 1917 年的展覽中展示了一個(gè)小便池,但在 50 年代成為一個(gè)懸而未決的問題,并且從那以后變得越來越難以定義。
波普藝術(shù)表明藝術(shù)和大眾媒體(例如廣告和漫畫)之間的界限正在消融。它的敷衍和大量生產(chǎn)的外觀是整個(gè)社會(huì)的外觀和沃霍爾及其產(chǎn)品的超然,空白品質(zhì)總結(jié)。平庸、道德失重、人格解體的圖像,被時(shí)尚意識(shí)的營銷策略玩世不恭地操縱:現(xiàn)代藝術(shù)及其世界的虛無暴露無遺。
60 年代藝術(shù)風(fēng)格和方法的激增——概念、極簡(jiǎn)主義、表演等——以及大多數(shù)藝術(shù)的加速過時(shí)帶來了“后現(xiàn)代”時(shí)代,現(xiàn)代主義的形式“純粹主義”被現(xiàn)代主義的不拘一格的混合所取代過去的風(fēng)格成就。這基本上是一種疲憊、無精打采的廢舊碎片循環(huán)再造,宣告著藝術(shù)的發(fā)展走到了盡頭。此外,針對(duì)象征性的全球貶值,它無法產(chǎn)生新的象征,甚至幾乎沒有努力這樣做。
有時(shí),像托馬斯勞森這樣的批評(píng)家會(huì)哀嘆藝術(shù)目前無法“激發(fā)真正令人不安的懷疑的增長(zhǎng)”,幾乎沒有注意到相當(dāng)明顯的懷疑運(yùn)動(dòng)可能會(huì)推翻藝術(shù)本身。這樣的“批評(píng)家”無法理解藝術(shù)必須保持異化,因此必須被取代,藝術(shù)正在消失,因?yàn)樽匀慌c藝術(shù)之間的永恒分離是對(duì)世界的死刑判決,必須廢除。
就其本身而言,解構(gòu)宣布了解碼文學(xué)的計(jì)劃,實(shí)際上是整個(gè)文化中的“文本”或意義系統(tǒng)。但是,這種揭示所謂隱藏意識(shí)形態(tài)的嘗試因拒絕考慮起源或歷史因果關(guān)系而受阻,這是它從結(jié)構(gòu)主義/后結(jié)構(gòu)主義繼承下來的厭惡。德里達(dá),解構(gòu)主義的開創(chuàng)性人物,將語言視為一種唯我論,受托進(jìn)行自我解釋;他不從事批判性活動(dòng),而是從事關(guān)于寫作的寫作。與其說是對(duì)沖擊現(xiàn)實(shí)的解構(gòu),不如說是一種自成體系的學(xué)院派,文學(xué)與之前的現(xiàn)代繪畫一樣,從不脫離對(duì)自身表面的關(guān)注。
與此同時(shí),由于皮耶羅·曼佐尼(Piero Manzoni)將自己的糞便罐裝并在畫廊出售,而克里斯·伯登(Chris Burden)的手臂中彈,并被釘在了大眾汽車的十字架上,我們?cè)谒囆g(shù)中看到了更貼切的寓言故事,例如繪制的自畫像阿納斯塔西——閉著眼睛。“嚴(yán)肅”的音樂早已不復(fù)存在,流行音樂也在惡化;詩歌瀕臨崩潰,從視野中撤退;從荒誕走向沉默的戲劇正在消亡;小說作為認(rèn)真寫作的唯一途徑被非小說所取代。
在一個(gè)厭倦、衰弱的時(shí)代,似乎說話就是少說,藝術(shù)當(dāng)然少了。波德萊爾不得不在一個(gè)沒有更多尊嚴(yán)可以分發(fā)的社會(huì)中要求詩人的尊嚴(yán)。再過一個(gè)世紀(jì),這種情況的真相是多么不可避免,而“永恒”藝術(shù)的安慰或站臺(tái)又是多么陳舊。
阿多諾是這樣開始他的書的:“今天不用說,任何關(guān)于藝術(shù)的事情都是不用說的,更不用說不用思考了。關(guān)于藝術(shù)的一切都成了問題;它的內(nèi)心生活,它與社會(huì)的關(guān)系,甚至它的生存權(quán)。” 但審美理論肯定藝術(shù),就像馬爾庫塞的最后一部作品一樣,證明了絕望和攻擊封閉的文化意識(shí)形態(tài)的困難。盡管哈貝馬斯等其他“激進(jìn)分子”認(rèn)為廢除象征性中介的愿望是不合理的,但越來越清楚的是,當(dāng)我們真正用我們的心靈和雙手進(jìn)行實(shí)驗(yàn)時(shí),藝術(shù)領(lǐng)域被證明是可悲的。在我們必須實(shí)施的變形中,象征性將被拋在后面,藝術(shù)被拒絕而有利于真實(shí)。在那一刻,游戲、創(chuàng)造力、自我表達(dá)和真實(shí)體驗(yàn)將重新開始。